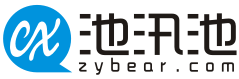小白是高二下学期转来我班的。在此之前,他是出了名的“问题学生”——上课睡觉、课堂捣乱、偷偷抽烟,因屡教不改已停课在家近一年。得知他要转入时,我本能地抗拒:没有哪个班主任不希望学生听话好学,我既担心教不好他,更怕他影响班级秩序。
初见时,是他父亲带着他走进办公室。男孩低着头站在角落,透着几分腼腆;父亲则不停搓着手,反复保证“孩子肯定守纪律,再也不调皮了”。交谈间,家长的无奈几乎要溢出来:“孩子还小,总不能一直在家耗着,现在不指望他多优秀,能顺利毕业就好。”
按惯例,这类学生入班需写保证书并由担保人签字,可在他父亲去取教材的间隙,我和小白有过一次简短对话。他说话时小心翼翼,紧张到有些结巴,那股藏在局促里的“想改变”的劲儿,让我动了恻隐之心。我决定撕掉“保证书”这层形式——与其要一份没有约束力的承诺,不如换一份他对我的信任。就这样,小白成了我班的一员。
nerror="javascript:this.style.opacity = 0;" src="http://wap.zybear.com/file/upload/202509/04/101259212.jpg" />
转天早读,我巡视时特意留意坐在最后一排的他,可一眼望去,血压瞬间飙升:他正和周围同学谈笑风生,完全没把早读放在眼里。昨天的信任、他的局促,此刻都像成了笑话。我强压怒火,把他拎进办公室,失望压得我说不出话。他红着脸反复道歉,我终究还是软了心:“再信你一次。”
往后几天,我格外关注他。我的课上,他听得格外认真,即便一轮复习已开始,落下的知识让他满脸吃力,却仍能看出对知识的渴望;自习课上,他也埋着头努力追赶。我立刻给小白妈妈打了电话,特意叮嘱:“等他回家,一定要说陆老师今天表扬他了,告诉他只要坚持,肯定能赶上来。”
本以为他会就此步入正轨——我的课堂上,他甚至会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可其他科老师的反馈却给了我一盆冷水:“小白上课总打瞌睡。”我起初不信,直到自习课上亲眼看见他趴在桌上,同桌使劲摇他都没反应。我拿起一本书拍在他后背,他惊醒后,才在办公室说出实情:长期熬夜玩手机到凌晨一两点,白天根本撑不住。
以往遇到这种事,我会立刻联系家长,但小白的情况显然是家长已无计可施。看着他低着头的模样,我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与其“堵”,不如“疏”。我和他订下“君子协议”:每天晚上十一点半前必须交手机给父母。他迟疑了许久,最终点了头。当晚十一点半,我收到小白妈妈的消息:“手机已经交了。”悬着的心,终于松了半口气。
nerror="javascript:this.style.opacity = 0;" src="http://wap.zybear.com/file/upload/202509/04/101300922.jpg" />
日子一天天过,学校摸底考试的成绩出来了——小白的物理竟然考了全班第一。我第一反应是“他作弊了”,可又怕冤枉他,便先找他聊生活和学习。他的话让我意外:“刚开始交手机特别不适应,可坚持一阵后,觉得玩手机也没什么意思。现在不怎么碰手机了,反而能学到半夜一两点。”原来,他是真的变了。
转眼到了高考,成绩公布时,所有人都很意外:小白离本科线只差两分。后来赶上录取降分,他如愿考上了理想的本科院校。
得知他要送锦旗感谢我时,我心里满是欣慰。再次见到小白,他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腼腆局促的男孩——阳光、自信,笑着朝我走来,活脱脱一个开朗的大男孩。
我想,这大概就是教育的意义:不是把所有学生都教成“尖子生”,而是用信任和耐心,帮他们找到向上的力量,让每个“差点掉队”的孩子,都能追上属于自己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