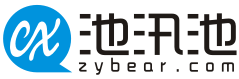近年来,我国即时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用户需求旺盛、消费场景丰富,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国家政策对即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2024年11月,商务部等7个部门联合印发《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支持“到店+到家”协同发展,推广线上线下融合的即时零售模式,为即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政策环境。当下中国,即时经济场景丰富,商家与平台积极参与,线上下单、线下送达的消费购买逐渐成为新常态,已成为我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时配送不再仅限于外卖服务,还涵盖日用百货、鲜花、急件等品类,且覆盖了广泛的时段和场景,如生鲜直达、节礼即配、跑腿排队等。2024年,中国即时配送订单量达到482.8亿单,同比增长17.6%。据市场机构估算,2024年我国即时零售市场规模约7800亿元左右,增长20%左右,今年将达1万亿元以上。
即时零售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消费者对便捷、高效购物体验的需求不断上升,以及新技术在零售领域的广泛应用。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消费者对购物便利性和即时性的需求不断提升。有报告指出,超过50%的“95后”希望在购物当天即可收到商品,且愿意为更快的配送服务支付一定溢价。随着“95后”乃至“00后”成为消费主体,购物需求更加细分和个性化,即时消费需求将不断扩大,即时经济将向全天候(消费者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即时零售平台购买所需商品)、全场景(即时零售不仅限于特定场景,而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多元化方向发展。中国即时配送订单量未来5年年均增长10%以上,预计到2030年有望突破千亿单。据市场机构估算,我国即时零售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有望突破2万亿元。
即时经济有很大潜力成为消费增长极,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中小零售商户的数字化基础薄弱、入驻电商平台成本较大;比如平台政策频繁变动且执行标准不一或缺乏稳定性;再如配送骑手权益保护问题仍然存在等等。在行业生态方面,商家常采用价格战等一些竞争手段,而平台则常通过补贴吸引消费者,压缩行业利润空间。当前,随着即时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竞争进一步充分,上述问题有望在发展中得到有效解决。此外,即时配送行业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对基础设施、物流网络、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更高要求,而加快适配即时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助于即时经济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
即时经济作为数字化时代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无论是扩大消费,还是增加就业,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全方位扩大内需,要把即时经济摆到更加重要位置,除健全相关数字基础设施等硬件,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外,关键是要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创造良好环境,有效推动即时经济成为我国新的消费增长极,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是要把握好监管边界,避免无限延伸。即时经济的监管边界,是当前数字治理的核心挑战之一,要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既要防范风险,又不能过度干预正常市场行为。监管应聚焦于可能危害公共利益的领域(如食品安全、配送安全、劳动者权益保护、数据安全等),对企业的正常经营策略(如定价模式、技术创新、服务优化等)不做过多限制。比如,可以要求平台企业审核商户资质,但不应直接规定平台的抽成比例或配送费标准。不要干预“技术创新”,而应聚焦于技术应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算法歧视、数据滥用)。又比如,允许平台用算法优化配送路线,但需监管算法是否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情况。
二是要创新监管模式,避免“一刀切”。即时经济依赖灵活性、时效性,监管需尊重其“行业特性”(如灵活用工),避免用传统行业规则来管新兴行业。国务院明确要求对平台经济“避免用老办法管理新业态”。比如,对网约配送员的权益保障,应探索适合灵活就业的制度(如新型社保、商业补充保险),建立适应平台用工特点的权益保障体系。要建立平台分级制度,根据平台规模、业务类型、风险等级(如涉及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金融支付等)实施差异化监管,对成熟业态、新兴模式、高风险领域的监管要求应该不同。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数字化监管平台,实现对违法风险的智慧监测、精准识别。
三是明确监管责任,避免转嫁监管压力。清晰界定即时经济参与各方责任,尤其是平台责任。明确平台在信息撮合、交易保障、服务标准制定、定价机制、纠纷处理、数据管理、安全保障等方面的主体责任。但不得将行政执法职责(如定价监管、资质审批)转嫁给平台。比如,平台仅需约束自营商品定价权,非自营商品定价权仍属商家。要明确平台的“有限责任”,不应要求平台对所有环节(如商户私下违规操作)负无限连带责任。比如,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要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经营者资质审核,严格落实证照审查和公示制度。商户食品安全出问题时,平台需承担审核不力的责任,但不应让平台为商户的故意违法行为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对网约配送员的安全教育。
四是建立高效协同机制,避免监管交叉或真空。即时经济(如即时支付、即时配送等)具有高度的动态性和跨地域性,其业务模式往往突破传统监管的时空限制。比如,数字企业通过数据和算法驱动,形成了“无边界”的生态圈,这与政府属地监管体制存在矛盾。此外,即时经济的快速迭代和不确定性也对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事后监管”模式难以适应。中央与地方、各职能部门(如市场监管、网信、交通、人社、税务、金融监管等)要加强在即时经济各细分领域(外卖、网约车、即时零售、跑腿服务等)的监管职责协同,避免出现交叉或真空地带。要探索新型监管模式,加强跨区域、跨部门协作,应对即时经济平台业务的跨行业、跨地域甚至全球性特征。
五是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避免大包大揽。即时经济涉及供应商、商家、平台企业、配送骑手和消费者等多方利益。监管要以维护“公共利益”为核心,不要介入企业之间的正常竞争,比如服务质量、价格差异的良性比拼等,而是要将更多管理协调职能交给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鼓励行业自律与多元共治,支持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规范、服务标准和自律公约,引导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探索支持劳动者通过合法途径(如行业工会、平台协商委员会)与平台进行集体协商的机制。鼓励消费者组织、劳动者组织、研究机构、媒体等社会力量参与监督,调动平台企业、劳动者、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多元共治格局,促进即时经济健康发展。
内容来源:新经济学家智库
责任编辑:张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