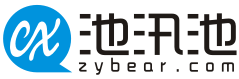“最近我也在新的平台更多思考AI和终端的结合,尤其对汽车和手机这两个最核心的终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启明创投·创业与投资论坛上,启明创投创始主管合伙人邝子平向他十多年前因AI结缘的老友——如今的千里科技董事长印奇,抛出了一个关于近况的轻松问题。印奇的回答,却直接将全场的思绪拉入到了当下全球AI产业最核心的战场。
他与邝子平的对话,虽然只有20分钟左右,但从技术范式、商业逻辑,到产业重构与创业哲学,高密度的信息,足以让现场听众“醍醐灌顶”。从AI 1.0时代的旷视科技创始人,到如今在“新的平台”上思考未来,年已超过“35 under 35”门槛的印奇,身上沉淀了中国第一代AI创业者特有的坚韧、反思与敏锐。
某种意义上,邝子平这次对话的印奇,作为一个连续创业者,在经历市场洗礼后,其对AI商业本质的深刻复盘,以及他口中的“闭环”与“飞轮”,为喧嚣的大模型时代,提供了一个相对冷静而务实的思考框架。
在探讨终端之前,邝子平首先将话题引向了产业的驱动核心——大模型。面对阶跃星辰、DeepSeek等国内厂商的密集发布,以及GPT-5即将登场的传闻,他请印奇点评中美大模型产业的现状与水平。
印奇没有直接给出简单的优劣评判,而是构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分析框架。在他看来,过去三年的大模型发展,可以清晰地被两条轴所定义。
“第一条轴,是学习范式,”印奇认为,“如果现在去硅谷和OpenAI、Anthropic、谷歌的人聊,大家已经比较清晰地会把整个未来学习范式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从最早的模仿学习(GPT的范式),到现在的强化学习,再到未来的自主学习。大家觉得可能通向AGI就是这三个范式的演进。”
他进一步阐述,范式的迭代周期大约在18到24个月。这意味着,从GPT-1到GPT-4的两年多时间,虽然模型能力在“量变”,但并未发生范式上的“质变”。真正的拐点出现在今年年初。“DeepSeek的爆发是全球第一个复现了O1这样一个强化学习范式的模型,且做了开源,做了非常好的体验。”他大胆预测,从今年年初到明年年末,将是强化学习的主场,因为其中仍有巨大的探索空间。为了佐证这一点,他甚至引用了一个可能被外界忽略的细节:“最近大家可能没有关注Grok4发布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值,Grok4显示它的强化学习计算量超过了预训练的计算量。”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一个模型今天还不以强化学习为核心,那么它可能已经不代表最前沿的技术方向。
第二条轴,则是对信息和数据形态的处理。“纵轴是比较清晰的,从语言到多模态、到世界模型。”在印奇看来,文生图的Midjourney和文生视频的Sora,正是在学习范式演进的间隙中,沿着这条信息形态处理的轴线所产生的技术变革。他给出了一个相对具体的时间表:“我们预测在未来6-9个月,对于多模态模型,会有理解生成一体化这样的核心技术的一些很惊艳的产生。”
在这个“3x3”的九宫格框架下,“今天比较统一的认知是中美在模型上差6个月左右的时间。”印奇说,“但是不是代表中美之间的模型差距缩小了呢?这个结论不一定是Yes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差异在于资源投入的战略方向。“如果我们看中美在整个算力消耗的量上,其实差距是在拉开的。也就是代表美国这些巨头在花更多的算力探索更多技术原创性的技术迭代爆点和断裂点,而中国现在短期内很多还是比较跟随和务实的态度。”
这并非悲观,而是一种清醒的现实判断。在他看来,中美将在全球AI版图中扮演不同角色,而中国,或许会在开源体系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分析完宏观的技术趋势,邝子平将话题拉回到创业本身,他邀请印奇分享从AI 1.0到2.0的心得——对于一家AI企业,如何才能真正走向市场,实现商业价值?
印奇分享的第一个关键词,是“闭环”。
他回忆起2011年刚创业时的情景,那时正值大学生创业热潮,当年的认知是“创业是先跳下悬崖,再组装飞机”。“我今天回头看,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印奇认为,AI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消耗资源极大、竞争最剧烈的行业。这种环境下,“在创业的时候,至少要把创业从技术到产品、到商业化的基础要素有个大概的设计。”创业过程中固然充满了未知,但如果商业模式的基础要素缺失或错误,“再努力可能都是往错误的方向狂奔。”
印奇给出了他对于技术与商业关系的最终论断,“我自己认为,不能闭环的商业模式是无法持续推动技术进步的。”
邝子平追问,技术进步与商业闭环本身就是互动的,如何更好地匹配?这引出了印奇的第二个关键词:“飞轮”。
他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CEO的“手感”。“当我们作为一个CEO运营一家公司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手感,推动着一个飞轮,这个飞轮可能会有很多变量。”
他将飞轮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小飞轮,常见于C端产品。“这个轮子推一推就转了,”他说,“当你面对用户需求和商业模式的时候,那个体感是很真切的。如果这个飞轮是小轮子,上来就推动推得很快,这个模式,就像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周志峰提到的‘go narrow and go deep’,你是会有体感的。”
第二种,则是基础大模型公司面对的巨大飞轮。“你会发现这是巨大的轮子,要花很大的能量,”印奇说,“但另一方面你会知道,如果这个轮子能够推得动,未来真的可以有巨大的商业闭环。”然而,推动巨大飞轮需要大胆的假设,但更需要回归商业常识。
现场,邝子平抛出了一个尖锐且现实的问题,堪称所有大模型创业者的“灵魂拷问”:“闭环和技术进步肯定是互动的,很多创业的新机会也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使用成本越来越降低,才能变成现实,这两者如何更好地匹配?”
印奇表示,“所有做基础大模型的公司都要回答——你的商业模式为什么能够每年付20-30亿的人民币在基础的算力投入上?如果你的商业模式发现5年后、10年后不可能有这样的利润,那你的商业模式是不成立的。”
这种在“大胆假设”和“回归常识”之间寻求平衡的思考,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从AI 1.0的理想主义走向AI 2.0的现实主义的深刻写照。
对商业闭环的深刻反思,自然而然地导向了印奇对当前AI创业赛道的判断。当邝子平问及他为何将目光聚焦于汽车和手机这两个“很硬、很花钱”的端侧时,印奇给出了一个看似悲观、实则充满机遇的分析。
他首先排除了纯软件App这条路径在中国市场的可行性。“我自己认为在中国的商业竞争非常难,”他直言不讳,“这里面有两家非常优秀和伟大的公司,一个是字节,一个是腾讯,一个是打先手,一个是打后发。”他以腾讯视频号成功追赶抖音为例,证明在巨大的赛道里,巨头的后发优势依然强大。
更重要的是,AI时代的竞争范式已经改变。移动互联网时代,今日头条可以从巨头忽视的角落“偷袭”成功。但在大模型时代,“这是一个明牌的、重注的、所有人都关注的行业。在所有人关注的行业里,我觉得是非常难出现‘偷袭’的机会,因为大家的信息量非常大。”人才、技术、想法的高速流动,使得创业公司几乎没有时间窗口期。“当然我可能因为第一段创业被毒打太多,所以偏悲观一点。”他自嘲道,但这份“悲观”背后是对中国互联网竞争格局的冷静洞察。
那么,机会在哪里?印奇将手指向了硬件。
“我觉得硬件有非常巨大的机会,”他强调,“不光是车和手机。”他认为,过去一些AI硬件(如AI Pin)的思路可能是错误的,它们过于执着于硬件形态本身。而在他看来,未来的逻辑将彻底颠覆。
“未来的AI服务、操作系统和硬件可能是一件事,”印奇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最终会发现,本质上应该是提供什么样的AI服务,硬件会变成非常载体化的东西。”
为了让这个略显抽象的概念更具象,他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
第一个是近期重新火爆的拍立得。“这是一个拍照又能够打印的相机,那就是所谓最好的AI服务,硬件形态不重要,最重要是说你要交付一个什么样的端到端AI服务。”他由此推论,“当我们在定义一个AI硬件的时候,你要先告诉我,什么样的AI服务是因为这个硬件,比在手机上装一个豆包要好?当这个服务成立的时候,可能会寻求一个最好的硬件形态。”
第二个例子来自大家熟悉的手机行业。“最近像小折叠的手机,会发现小米卖得好,原因是我们发现小米有非常好的照片打印机,能把这套闭环掉。”
这两个案例精准地指向了他对未来AI终端的构想:产品的发布会,应该首先阐述创造了一个多么优秀的Agent(智能体),以及这个Agent为何如此好用,然后才介绍,“我给它配了如此丝滑的硬件,让他体验上很闭环。”未来的终端,将真正走向场景化和服务化。
这场终端革命的另一大变量,是操作系统。
“未来的手机是人机共驾,”印奇预测,“机器可能在后台做非常多的事情。”这种人机交互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将驱动操作系统的本质变化。他抛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大概率发生的事情,比如未来的Gemini,就会上全球非中国区域所有安卓的手机。如果是这样的话,全球Gemini Agent的日活会超过3亿,会变成全球最大的Super AI App。”
在AI Agent与操作系统的双重变革驱动下,硬件将衍生出多样的形态,再逐步收敛。而这个充满变数的领域,恰恰是巨头和创业公司都能找到机会的沃土。
对话的最后,邝子平从投资人的视角提出了终极问题:在手机和汽车之外,是否存在一个全新的、能够承载所有服务的单一平台级硬件机会?
印奇认为,中国的硬件格局已经形成了以华为和小米为代表的“人车家”生态范例。
人:这个生态以手机为绝对核心,包括智能穿戴、智能眼镜等设备,都将是依附于手机生态的子品类。他对于出现一个独立于手机的、巨大的个人终端机会“要打一个问号”。
车: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场景。“智驾、智舱刚刚兴起,Robotaxi虽然讲了很多年,其实还在一个爆发的前夜。”他对此十分笃定。
家: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场景,未来可能成为具身智能的核心载体,但他判断其爆发周期会更长,在五年以上。
在这三大显性机会之外,他还指出了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创业机会。“之前我也听到投资界有个说法,中国以深圳为基地,有很多大概100万台一年(出货量)左右的机会。”他认为,这些面向垂直领域的优质硬件,是启明创投这类机构非常好的投资标的。在这个100万到500万台出货量的区间内,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创业机会。但如果要追求千万甚至五千万台以上的巨大成功,创业者依然需要回到“人车家”的宏大叙事中,去寻找潜在的可能性。
这场对话,没有太多宏大空泛的叙事,而是充满了“闭环”、“飞轮”、“体感”、“ROI”这样朴素但直指商业本质的词汇。印奇从一个技术理想主义者,成长为一个深刻理解商业规律的务实主义者,其心路历程本身就是中国AI产业十余年发展的缩影。
而从模型的“九宫格”到商业的“闭环论”,再到终端的“服务先行”,未来的三年,可能是AI与终端结合的“非常有意思的三年”,那些真正能理解并践行“闭环”与“飞轮”理念的人,或许才能在这场关乎产业重构的进化论中,最终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