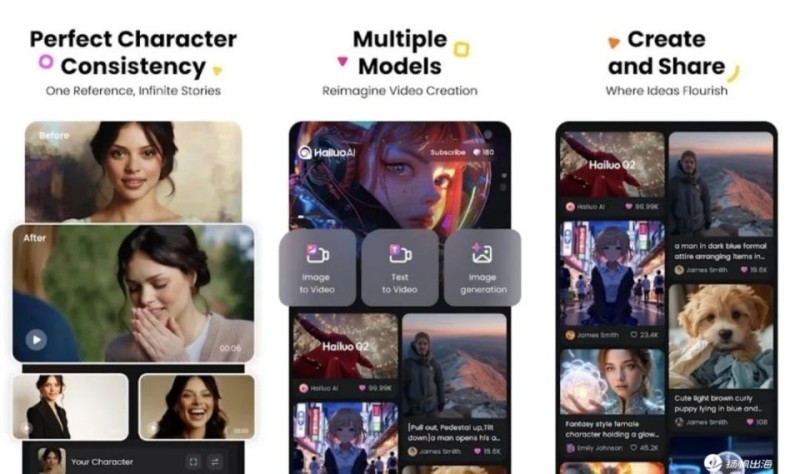革命传统的再造与自我认同的辩证
——评西元小说《逆流而上的大山》
崔庆蕾
和平年代的军旅文学该如何书写?如何在有限的故事母题中衍生出新故事?如何将纯粹与统一引向多元与复杂?如何在传统书写范式与叙事经验中重铸新的时代精神?这些都是当代军旅文学创作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返观当下文学现场,一些颇具探索性的军旅创作愈显珍贵,西元便是其中的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优秀代表之一。他持续推出了一系列书写革命历史或反映军旅生活的作品,如《遭遇一九五零年的无名连》《死亡重奏》《炸药婴儿》《大校、上尉和列兵》等等。但西元的创作并不拘囿于此,并不止步于对军旅生活的描摹和历史事件的重构,而是在此框架之下努力扩展叙事边界和表现方式,多向度探讨形而上的生命议题,充满哲思与审视,具有一种难得的探索精神。如同徐勇所指出的,“他的小说兼具问题小说、现代批判和人性探索于一身”①。这种积极的探索姿态在中篇小说《逆流而上的大山》中愈发凸显。
一 革命传统的再造:
战争、死亡与英雄主义精神
西元的小说注重对革命传统以及英雄主义精神的重塑和召唤,《逆流而上的大山》延续了这一主题向度,对革命传统的再造,对英雄精神的重构成为该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小说以1950—1960年代开展的军事试验为背景,通过魏老骡子、魏大骡子、魏小骡子三代人的故事,书写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后的宏大历史变迁,并以两个重大历史事件重构了革命传统以及带有理想主义的革命精神。作品中的抗美援朝战争与在西北戈壁滩的军事实验构成了一条军事叙事的线索,从战火纷飞的抗美援朝战场到静寂无声的西北荒漠,都是军人的战场,都是锻造革命精神的熔炉,都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作品中,这两个战场是用同一组军人串联起来的:张司令、常政委、李大耳朵、赵大钳子等人,他们既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主体,也是戈壁滩军事实验的主体。两个场景横跨革命与和平两个历史时期,一定意义上,正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的一种象征统一。
两个战场归属不同的性质,但在内里却显现了革命传统的传承与再造。在抗美援朝战场,直面生与死的考验成为每位战士的必修课。在魏老骡子和赵大钳子的对话中,不乏战争场景的细致描述,“进了坑道一看,我就明白了,也就没再打算活着下高地。咬牙扛着吧,扛到死为止。每个人都得在死这面镜子前照照自己。我们和敌人都得照,谁怕了,谁就输了。结果呢,是敌人先怕了。”惨烈的战争锻造了高度统一的不怕牺牲的英雄精神,这种精神成为赢得胜利的支撑性力量。而在个体层面,经历血与火的淬炼,对生命的本质性理解,对家国情怀、民族命运的认知都有更深层次的跃升。李大耳朵在回忆战争时对魏老骡子说,“可以不死了,去哪儿都是享福啊!”这种超脱的生死观即是战争本身的“后果”,是生死边缘淬炼出的深层认知。
除了重构这样一种革命精神,作品触及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这种战争时期锻造的革命精神在和平年代如何进行传承、转化与再造?和平时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虽然刀枪入库,但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并未停止,如何激发一种历史精神的当下价值,赋予其新的动能和意义是每个时代的共同课题。在这篇作品中,作者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处理。赵大钳子谈及荒凉的戈壁滩进行军事实验的任务时说:“我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又让我来这个苦地方,跟我讲多少大道理我都听不进去。但你要说来这儿是弄那个能响的大家伙,那我可就来了精神啦!唉!他娘的,那一仗打的……”随后,赵大钳子又狠狠地作了表态式总结:“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在这里,作者通过赵大钳子将抗美援朝战争与军事实验进行了有效的接通。一方面,他是两次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在主体身份上具有连接性和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在这一人物的精神内部,有对两次事件的对比和转化,抗美援朝战争的惨烈激发了赵大钳子投身于军事实验的动力和热情。在他眼里,军事实验也是战争的一部分,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进行艰苦的军事实验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打赢战争,是为了更多军人的“生”和国家更好地“强”。由此,抗美援朝作为一个事件成为了推进军事实验的新动力,也将一种在战火中锻造的革命精神成功进行了转化,融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中去。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历史精神被重新激活,从而具有了当代价值和意义。
而这种价值观的背后同样闪烁着英雄主义的光芒。虽然没有在战场上牺牲的崇高与壮烈,这样一批投身军事实验的军人实际上仍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一方面是显在的牺牲,比如,刚刚抵达戈壁滩时魏老骡子看到的那个从铁塔上因大风掉下来身亡的无名战士,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个体生命。另一方面是隐性的牺牲。军事实验会对人的身体带来伤害,当实验出现问题,科学家老王毅然决定去一线勘查时,现场充满了担忧与悲壮(一同前去的魏大骡子没有生育能力构成对此的强烈隐喻),他们以血肉之躯构筑起英雄精神的界碑。在作品中,一种将“小我”融入“大我”,将个人融入集体的崇高英雄主义精神始终在闪闪发光、澎湃激荡,这种精神贯穿了革命与和平两种不同的历史语境,实现了有效的对接与转化,并重构为新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军人以及科研工作者都是“逆流而上”的人,都是在极端困境和挑战中成为了历史推动者的“大写的人”。
二 自我认同的辩证:
“到世界中去”与“回归原点”
西元的小说总是充满对诸多形而上议题的思考,在军事叙事之中融入生命哲思,兼具形而下的描述与形而上的追问。比如在《死亡重奏》中对于死亡的深度思考,《大校、上尉和列兵》对信仰问题的不懈追问,都令人印象深刻。《逆流而上的大山》除了重构一种革命传统,同时融入了作者对于自我认同的深入探讨。这一主题比较突出地蕴含在魏小骡子和英子等青年一代的故事之中。
在作品的众多人物之中有一组矛盾尖锐的父子关系:魏大骡子与魏小骡子。两人之间虽无血缘,但这组对照是作者对中国式父子伦理的深度思考,凸显出一种传承的疑难与自我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典型地体现在反复出现的“大山”意象中。在小说中,“大山”具有多重隐喻。它既是一种自然风景,是军事实验的物理环境,也是魏小骡子艺术创作的现实对应物。但它又不仅仅具有物理意义,同样隐含丰富的象征意义。首先是一种在层层围困之下,百折不挠、逆势而起的积极向上的生命精神。比如,那些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又投身军事实验的军人们、那些为了研发新武器而默默进行科研的研究者们以及融入部队作出了贡献的魏老骡子们,都具有这样一种可贵的生命精神。其次是坚持自我并不断追寻自我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反抗精神。在作品中,魏小骡子始终在与整个生存环境以及父亲魏大骡子进行对抗,体现出一种“逆流而上”的反抗命运的精神。在戈壁滩上,魏小骡子浓郁的艺术感与整个环境的严整性存在强烈冲突,这让他成为一个“异数”。当他带兵时,他是他们的兄弟而不是长官。当他写报告时,他只能用画来表达他的抽象想法,却不会逻辑推理和数据分析。当父亲希望他成为科学家时,他沉迷于画画。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被投放到不合时宜的环境中的悲剧性人物,是一个边缘人,但他的内心又始终有所坚持,有所追求。他以画笔为武器,留下了自己的生命足迹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他的生命也是一种“逆流而上”,是对一种环境生态的反抗,也是对一种家庭秩序的解构。
戈壁滩生活的高度严整性与贫乏性,与青年一代的生活理想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内在冲突,导致青年一代自我认同的危机与迷茫,并由此引发“到世界中去”的强烈想象与渴望。这一问题比较明显地体现在魏小骡子与英子的爱情故事里。作为从戈壁滩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他们虽然在这个闭塞的环境中长大,但始终有一种重构生命、接通与更广大的世界的愿望。在高考前,英子对魏小骡子说:“我很怕。我之所以一心想要到外面去,就是因为我不知该去哪里。”青春期的迷茫与寻找自我的诉求萦绕于心头眉间,“到外面去”成为她的人生动力与支点,“外面”与戈壁滩构成两种不同质地的世界。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敏锐洞察“到外面去”与“回归原点”的辩证关系,“到外面去”仅仅是一种行动的方向和愿景,并不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实现尤其是精神家园的建构,“回归原点”也并不意味着一种封闭和无意义。英子的求学之路顺风顺水,工作上也一路畅通,成为某跨国科技公司负责技术研发的副总裁,但她并未真正找到安放自我的精神家园。当她与魏小骡子终于在多年后重逢,魏小骡子问她:“你找到了要去的地方了吗?”英子说:“没有呢。有点像佛家说的,在世上转一圈,无所从来,也无所而去。当年,是那么想离开这儿,可走来走去,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轻得像一片叶子的游子。”她虽然事业有成,却像无根的浮萍。她的生命与魏小骡子的生命构成了一组对照性的镜像,映照出生命本身的内在悖论与辩证。家园何处?心归何处?正如从北京来的科学家老王对于生命的认知:“人类进步的历史恐怕也是如此吧!什么帝王将相,什么英雄豪杰,什么才子佳人,什么灯红酒绿,什么车水马龙,什么功名利禄,不过都是浮云,他们不是历史的真面目。我们要去的地方其实一直就在我们心里。我们走来走去,其实都是眼前的这盏灯光在照亮前方的路。所以,不要因为身处蛮荒之地就彷徨无定,看似最远的,或许正是最近的。如果你在做正确的事情,无论你在哪儿,无论你现在看起来多么弱小,世界终究会向你走过来的!”魏小骡子与英子用不同的生命经验和历程验证着这一论断,于生命而言,“到世界中去”与“回归原点”构成辩证关系,世界不在远方,而在所置身的脚下。
同样引人深思的,还有魏小骡子与父亲魏大骡子的和解。当他在生命的最后终于与父亲殊途同归时,他获得了一种生命的释然,横亘心中多年的不解与怨恨也随之消解。而带来这种和解的正是他对生死的顿悟以及对生命本身的重新理解,“人的生与死之间有一道门槛,可这门槛当真是无法跨越的吗?如果可以迈过去的话,那是什么呢?肯定不是这个肉身的我,也不是灵魂,而是对未知的无穷无尽不受束缚永不止息的想象力。命运把我剥夺得一无所有,可我手中还有这一柄利剑。就算我倒下了,它的寒光依然吓得命运后退三步。死啊!你再也不可怕了,你看无数的勇士正手持利剑冲过你貌似固若金汤的防线。”魏小骡子一生困于父志传承,但他始终逆流而上,葆有真实自我,听从内心声音,他笔下那些怪异的大山正是他生命呐喊的象征,“红色的大山充满天地间,山峰和山脊像是公牛鼓胀的筋肉。大山又好似透明了一样,血红之下,是一条条金黄色的贲张血管。粗的血管仿佛奔涌着洪水,细的血管仿佛遮天蔽日的蛛网。大山好像一头愤怒的,又不甘心被宰掉的猛兽,对着天空嘶吼。”魏小骡子笔下的大山始终是抽象的、涌动的、勃发的,带着一种冲决一切的愤怒和力量,释放着生命的原初激情。相比于那些经历了战争洗礼的军人们,魏小骡子等和平时期的军人们对于生死的理解经历了更为漫长的生活洗礼。
总体而言,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元风格的小说。一方面,有着对于革命史重构的努力,在战争与建设的变奏中呼唤一种正在远去的革命传统与英雄精神。另一方面,又在微观层面聚焦个体的内在精神,在如何进行自我价值实现上进行深度追问,充满哲思。两个向度构成补充和呼应,也形成张力,带来叙述上的难度。如何更好地将哲思与观念融化为小说的丰富细节,形成更严密的小说逻辑,依然是一个有待继续思考和持续提升的方向。
注释:
①徐勇:《社会转型、生活政治与传统重造——关于西元小说的几个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