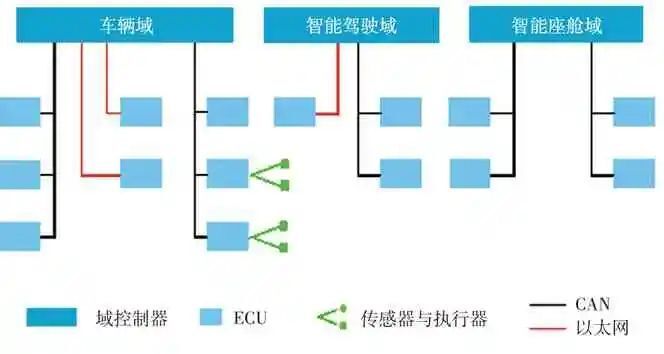◆《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1963年,日本文坛巨匠井上靖以《风涛》为其西域小说系列收官。这部以元初蒙古东征日本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并未如传统军记物语般铺陈战争场面,而是将镜头对准风暴眼中的高丽王朝,以“风涛”为隐喻,在惊涛骇浪中勾勒出弱国在强权夹缝中的生存困境。井上靖以克制而诗意的笔触,将历史文献转化为充满宿命感的文学叙事,让读者在平静的文字下触摸到历史的震颤。
弱国的生存史诗
《风涛》取材于1274年文永之役与1281年弘安之役,但井上靖刻意淡化战争场景,将叙事重心置于高丽君臣与蒙古帝国的周旋。小说开篇即以高丽太子倎的视角,展现蒙古铁骑踏破开京的惨状:荒芜的田野、逃散的百姓、被征作马厩的寺院,这些细节如刀刻般勾勒出高丽作为“跳板”的悲剧命运。井上靖的史观在此显露无遗——他通过高丽元宗与忠烈王两代君主在蒙古高压下的挣扎,揭示了小国在强权政治中的生存法则:反抗即亡国,屈从亦亡国,唯有在夹缝中寻找喘息之机。
这种叙事策略与井上靖的治史态度密不可分。他广泛引用《高丽史》《元史》等史料,甚至直接挪用忽必烈诏书中的“勿以风涛险阻为辞”作为书名,将历史真实转化为叙事基石。但更关键的是,他并未止步于史料复述,而是通过虚构高丽重臣李藏用、金方庆的心理活动,为冰冷的史实注入人性温度。例如,当蒙古要求高丽拆除江都城墙时,元宗与群臣的辩论既符合历史记载,又通过细节补充(如“倎急着赶路,主张强行渡河”)展现人物性格,使历史事件成为承载人性挣扎的容器。
自然与政治的双重奏鸣
“风涛”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其表层指向对马海峡的惊涛骇浪——两次东征均因台风(日本称“神风”)而败,但井上靖更将其深化为政治格局的隐喻。蒙古帝国对高丽的征服,本质上是更大规模的风涛:忽必烈通过怀柔政策将高丽绑上战车,使其成为侵略日本的先锋;而高丽朝廷内部,文相李藏用与武相金方庆的派系斗争,则如同海面下的暗流,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抵抗力。
这种隐喻体系在小说中呈现为多层次的张力结构。自然层面的风涛(台风)与政治层面的风涛(蒙古高压)相互映照,形成宿命般的循环:高丽因蒙古胁迫而东征,又因自然之力而免于灭顶之灾,但这种“幸运”背后是更深重的苦难——为筹备东征,高丽“四野凋敝,民不聊生”,百姓为制造战船砍伐山林,导致“连翘那黄色的花朵”成为旧都开京仅存的记忆。井上靖通过这种张力,揭示了历史洪流中个体的渺小:无论是高丽君主还是普通百姓,都只能被风涛裹挟前行。
在历史废墟中寻找尊严
尽管《风涛》笼罩在宿命论的阴影下,但井上靖仍通过细节描写为人物保留了尊严的微光。高丽太子倎在蒙古大汗蒙哥驾崩后的表现堪称典范:当蒙古将领也速迭儿以“王京是否撤出江都”为借口威胁进攻时,倎以“将军说的话算不算数”进行反击,既维护了国家尊严,又避免了激化矛盾。这种“以柔克刚”的智慧,与井上靖在《楼兰》《敦煌》等西域小说中塑造的坚韧形象一脉相承。
更值得玩味的是,井上靖通过高丽群臣的日常生活细节,消解了历史的宏大叙事。例如,倎在前往蒙古途中对“连翘花朵”的回忆,李藏用与金方庆在朝堂上的默契对视,这些瞬间将历史还原为具体的人性体验。正如日本文艺评论家筱田一士所言:“井上靖的历史小说,总能在史实与虚构的平衡中,展现一种超越时代的悲悯。”这种悲悯在《风涛》中体现为对弱国生存困境的深刻理解——当倎在六盘山感受到蒙古军营的异常气氛时,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一叶扁舟”,但正是这种清醒的认知,赋予了他抗争的勇气。
历史小说的现代性启示
《风涛》的魅力,在于它既是一部严谨的历史小说,又是一部充满现代性的哲学文本。井上靖通过高丽的命运,探讨了强权政治下的道德困境、个体在历史中的位置等永恒命题。当读者合上书页,脑海中浮现的或许不是蒙古铁骑的威武,而是倎太子在异国他乡的孤独背影,或是李藏用深夜独坐书房的沉思——这些画面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记忆。
在当今世界,风涛依然未息。《风涛》提醒人们,历史从未真正远去,它只是以不同的形式重复自身。而文学的价值,正在于为这些重复的故事注入新的思考,让人们在风涛中看清方向,在黑暗中坚守光明。(2025年7月30日写于东京乐丰斋)